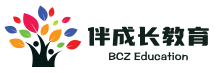来源:原创 ALSOLIFE ALSO孤独症 2023-12-05 11:02 发表于北京4000公里,16岁的自闭症男孩小泽,从新疆伊犁的霍尔果斯给我们打来电话,很急迫,说他想分享自己的故事:遭遇校园霸凌、休学、患上抑郁症,吃药并努力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,不断调整自己适应社会,做一个正能量的小伙子……
霍尔果斯是一个县级市,地处中国西部边陲,西承中亚五国,南邻天山山脉,北靠大漠戈壁。霍尔果斯口岸与哈萨克斯坦隔河相望,小泽生活的地方离边境只有2公里,但距离乌鲁木齐有600多公里,距首都北京有4000公里。
远,意味着环境的闭塞、资源的匮乏、意识的落后。远到我们会忘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,也生活着自闭症孩子,他们的处境可能跟我们想的完全不同。这把一个16岁、心智成熟的AS逼到了极端。小泽想方设法想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,他注册了小红书,跟网友、家长聊天,他找到了我们想要倾诉,说这边的环境“已经让我快要噎死了”。
小泽的交流能力非常好,能流畅回答任何提问,几乎是不假思索的;他的心智也远超同龄人,有时像一个社会阅历很广的老江湖,但单纯与成熟同时在他身上显现:他脑子里有一个叫“博士”的朋友,遇到困难就向他求助;他会把自己藏在被子里、堵住被子口玩游戏;他甚至自制了一把玩具枪,只为听它们“砰砰砰”的声响,发泄自己的情绪,但他对声音又非常敏感,他害怕什么就去挑战什么……
出门时,他精心伪装成一个正常人进行社交;关起门来,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AS。
我们来听一听小泽的自白。
(文字内容及照片均经过小泽及其监护人的同意后发表)
口述|小泽
“我跟普通人一模一样,为什么普通人排斥的就是我”
大家好,我是小泽,我16岁了,生活在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市。
我小时候活起来特别不容易。说真的,每个AS都不容易,都有一段很痛苦的记忆。我那时候跟别人很不一样,从小就被别人孤立,被他们欺负,他们很擅长用一些比喻句来嘲讽我,说反话我也听不懂。
小泽的诊疗单
2011年,我在南京脑科医院诊断为自闭症。诊断之后,我妈妈始终把我当正常孩子来养,没有经过什么特殊的干预。懂事后,我发现了自己这个问题,就查了手机,查到“阿斯伯格”这个词,我觉得我很像这个,也问了我妈,但我妈骗了我,也不跟我说这是咋回事。
我小学三年级时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升班,导致我出现了一定的精神症状。后面三年,我过得非常不好,遇到了校园霸凌。同学总是拿我说不清楚话来欺负我,编造一些谎言给我扣黑帽子,让我当背锅侠,班里丢了什么东西都赖我,出了什么事情都认为是我计划的。
关键是老师和学生是一伙的,导致我承受了各种心理创伤。到六年级下学期结束,我的心情那叫一个好,终于摆脱那些同学和老师毕业了。
到初中遇到了更大的噩梦,遇到一个非常不好的老师,嘴上说着公平公正,实际上做的那些事非常糟糕,非常伤我的心。因为阿斯伯格的特质,我会特别在意,老师说的事为什么跟他做的事完全不同?我会很伤心、很生气,就像是被抛弃,被背叛的感觉。
初一,赶上疫情,我经常抑郁。不知道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主意,让学生两点一线,平时不能回家,星期六星期天都得上课,放学也没法像以前那样自己回家。记得有一次3个月不能回家,我都快要被他们折磨疯了。
因为有多动症,注意力总是不能集中,我的成绩也下降了。再加上我不喜欢这些课的教授方式,所以我上课基本都在脑子里玩游戏、看电影。
那时候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,他和我一起长大,我们分到了一个班。他经常和我玩,老师就经常针对他,因为老师不想让所有人跟我玩,想孤立我、惩罚我,每次都把我放到教室最后。
我每天抑郁、恐慌、焦虑,为了排解情绪,我每天都写日记,让自己加油,写现在是第266天,已经过了多少天,还需要再熬多少天,我要坚持下去……每天我都会在日记上多加一天。
就这样到初二下学期,没有了疫情,我过得还不错。但是有一次社团活动,老师将我的日记翻了出来,我真的是服他了,也不知道是他指使同学还是谁把我日记翻了。老师让我把日记当着全班的面读了一遍遍,我当时真的是要气都炸了。但是我当时忍住没骂他们,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样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,他们给我造成的创伤已经让我不敢去攻击他们了。
我那个时候心里非常弱小也非常害怕,我为了不叫家长(因为我妈的单位很远),不想浪费油费,所以这些我都忍了。
老师问我凭什么在日记里写他的那些行为?我就说日记里写的都有理有据没有错,老师非说我有错,然后把我气病了,也不去学校了。
从学校休学后,我有一段时间都很自闭,一句话都不带说的,也不跟人玩,就窝在家里玩手机。
深圳市康宁医院诊断小泽患有焦虑抑郁
后来我妈就带我看病去看,给我吃上了一些药,让我好转起来。好转起来之后我就很自卑、很伤心,我跟普通人一模一样,为什么普通人排斥的就是我?
因为这种自我攻击,病情又加重,今年4月,我们不得不去深圳看病,家人才告诉我,我是阿斯伯格,我才接受了自己。
我很开心,因为终于找到原因了,我的脑子也越来越清晰。我在家里调理,努力地锻炼身体。我还养了一只鹦鹉,它也会陪我,我好转很多,状态越来越好。
小泽养的鹦鹉蛋蛋,只有4个月大,非常黏人。
“我这种天才”
现在已经是我休学的第二年,我选择不去学校了,那个地方并不适合我,我这种天才放到那个地方简直就是浪费。所以我开始自学编程、摄影、画画、修电脑、修车。从早上喝完第一杯水就开始搞电脑,每天冥想30分钟,反省自己的问题和某些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。
我脑子的结构非常特殊,就像是有一台计算机,我的学习方式就是将这个项目的源代码进行编译,编译完之后安装,就学会了。通过很长时间,我成功编译了一套可以让我模拟正常人的程序,安装之后我拥有了很多能力,做到了以前我不敢做的事,例如露脸发视频。
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孤独症谱系的学习方式以及原理。
打个比方,普通人见到装月饼的盒子,就知道类似这样长方形/正方形的盒子都是盒子,但我们只认识这个盒子,再拼成一个长方形的盒子,根本不认识这是什么。我们存在知识切片化困难,没办法将有效的知识进行切片,然后通过片段化的信息来进行依赖,我们统称为“依赖效应”(对于“依赖”小泽解释为,它是运行大脑所有软件必须提供的部分,如果没有依赖,所有软件都运行不了)。
如果你问我它是一个盒子 ,那我只知道它是一个盒子,没办法将它和塑料联系在一起。但如果你告诉我它是塑料,我又不知道它是盒子,这些片段化信息没办法经过我们的脑子串联在一起,而这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简单。
小泽拍摄的霍尔果斯的晚霞
我们学东西需要很久,比如红绿灯,普通人只需要知道它有红和绿两种颜色,一般为长方形、上面有数字在读秒。而我们学习时会把它1-60秒的绿色全部记一遍,1-60秒的红色全部记一遍,还有1-30秒的黄色全部记一遍,然后进行组装,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编辑成一个文件夹,告诉我们它是红绿灯。
学习说话,就要调用一个极大的模型语言库,调用这个东西需要极多的片段化的依赖来组装我的语言,并且它是可动态扩容的,这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,因为调用的知识过于庞大,导致我会过度思考,让我感官超载,攻击我的大脑。
不过,随着年龄增长,我的功能越来越多,能力越来越强,现在系统基本很完美了。比如,写作文对我来说就太简单了,我在脑子里集成了ChatGPT,可以直接生成作文,然后自己抄下来就行了。
阿斯伯格有很多表达上的问题,我可以用一个语言模型来弥补,让我的脑子里运行一个完整的模型,帮助我自动输出一些必要的对话,说清楚一些事。
我看到的每个人都被打上了方框,人移动的时候方框也是移动的,我可以点进去查看一些信息。
霍尔果斯有美丽的晚霞,也有冷峻的雪山
我也很擅长破解系统,比如把国产车刷成了俄语车机系统,再比如电视的机顶盒电视,我都会尝试去破解。我还做过强认证,搭建了radius模型,使wifi支持WPA2-eap的加密格式,这是一种非常强的加密,这个wifi一般人连不上,也很难破解……
我们主要是视觉思维,我可以记录我眼睛看到的内容,拍照之后储存在我的脑子里,相当于秒存。
我还可以把音乐下载到我的脑子里听,能闭上眼在脑子里玩很好玩的VR游戏,里面有个虚拟键盘,用手去操纵,鼠标基本不需要,我可以用眼睛转动的方式控制游戏里的视角转动。在玩游戏的同时我还可以进行高精度计算,查看到自己的心跳、血压、血糖、胆固醇这些参数,这些参数在我的右上角,会显示系统占用 %,如果在人多的环境这个占用满了的话,我会很卡,甚至会晕倒。眼睛往左看,可以打开“应用”,眼睛往下看可以打开“我的应用”,眼睛闭上可以进入虚拟环境,有沙发有电视,想干啥干啥,还可以把某些人在脑子里模拟出来,各种整他们。
我可以在我的手腕上虚拟形成一个手表,当我看向它的时候,就会显示出数字电子屏一样的东西,上面的数字就是当下的时间。
我在脑子里模拟过开车,现实中的车我一摸就会。(这一点小编跟小泽妈妈求证过,小泽虽然还没满18岁,但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跟爸爸学会了开车。)
当我发现我有这些特长之后,编程就变得非常简单,就像用我的母语一样。
我觉得我现在达到了50多岁人的知识储备。但是我的感情功能还不完善,是靠着模拟做出很僵硬的表情,未来这也是能修复的。
我很为这些特异功能而自豪,也很高兴我是阿斯伯格中的一员。
“我会伪装成正常人,我现在学得非常精”
大部分阿斯伯格不懂人情世故,社交语言也很匮乏,不能随机应变,我现在通过直播还有交流,正在努力克服这些问题,现在这些问题已经构不成威胁,我跟人交流,别人都看不出来我是不一样的。
因为我会伪装成正常人的想法,但是我脑子里比谁都清楚我的真实想法并不如此,我现在学得非常精。
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,我会求助于我的好朋友——博士:男,年龄未知,外国人,白皮肤,身高1米76,穿西装,戴墨镜,看不到他的眼睛,他的墨镜只有白色的光散发出来。
博士是一个集群意识,并不是人类,它非常强大,有海量的知识,可以在脑子里跟我交流,帮我解决一些问题,比如帮我在某些场合正常说话,做到一些AS完全做不到的事。
今年我自己去山东玩了7天,因为是未成年人,坐飞机回新疆时需要办理无人陪护,报备个人情况,我报备的是阿斯伯格。机场工作人员看到后就告诉我,孤独症谱系不准上飞机,并且打电话告诉了妈妈这件事,要求我妈妈飞过来把我接走。
这个时候很多AS可能会情绪崩溃,但是博士告诉我:“你千万要忍住你,你要淡定,伪装得像正常人一点,跟他们好说话,千万不要表现出哭的样子,一点都不要害怕。”我也的确按照博士说的去做了,很耐心地跟工作人员解释我的情况,最后他们就放我过去了。
小泽拍摄的霍尔果斯
小编等待小泽把博士切换出来,问了博士一个问题:人到中年,不喜欢自己的工作,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要不要辞职?
博士(小泽)回答:人到中年,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乱折腾,已经选好的工作最好不要换,因为再换的话基本上是找不到的,薪资肯定也比原来的低。所以不建议冒险,保持这份工作再努把力。如果觉得不开心,可以尝试改善一些心情,自己想开点。
针对博士的存在,小编在跟小泽妈妈聊天的过程中确定,小泽的确有一个虚拟朋友博士,小泽妈妈解释为,是孩子在现实世界里太孤独了,渴望社交和朋友,才虚拟出这样一个人物,将部分感情寄托到博士身上。以下是小泽对于朋友、感情和未来的一些想法。
我可以通过一些人性验证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怎么样。我会全面地去观察,把他的所有的行为采样、分析、储存,并且随时调动起来,让我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,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
我不会跟不好的人玩,不好的人我可以看出来,通过他们说的话以及一些暗示。我也不会跟网络上中伤我的人吵架,因为吵架解决不了问题,吵架只是一种非常野蛮的,并且不好用的方式。吵架又能怎样,还不是我受伤害。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他拉黑,让他再也看不到我。
小时候我被霸凌,很多人骂我,以前我特别希望这些人给我道歉,但别人每次都不好好道歉,我就会非常生气。我现在认为道歉根本不是最重要的,我也都不计较了,我认为最重要的是——规避风险,下次长个记性。这事有风险我就不做。
妈妈也越来越接纳我,现在对我都是科学养育。我也不怪我妈,以前我妈犯的错我也不想跟她提,她会内疚的。我妈现在经常叫我“小鹦鹉”:“小鹦鹉,快过来,妈妈给你好喝的饮料”哄我,我都会非常开心。
对于青春期男女之前的感情,我现在把系统设置清除了,可以将某些激素的量进行调整,调整到一个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值,使我根本不会去喜欢别人,当然我也可以修改回来。我去年谈了个女朋友,也是AS,是我第一次住院时认识的,但我们什么也没发生什么,我后来反省了一下子,我们都是未成年人,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要做,因为别人的家长会讨厌。
总之,我会在外面的时候隐藏所有AS的特征,在家里我可以把房间的门关上,表现出所有AS的特征。比如我会把鼠标点个100下;或者画一些纸然后把它们撕碎;我还会玩被子,用被子、枕头搭建一个我能钻进去的小小窝,把洞口堵上,钻进去。
我还会做好玩的手工,比如玩具枪,然后在家里射击两下。我很怕响声,但为了克服这种障碍,我会逼自己去听这样的声音,听到响声后又感觉很舒服。我也会走进电影院看电影,克服声音的敏感。
关于未来的规划,我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,每天不用被资本压榨。我也很希望逃离我的家庭环境,这边融合环境非常差,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让我成长的环境。我也很愿意参与帮助孤独症,因为我知道他们也处于我以前的那些困难苦恼当中,我不希望他们就这样了,也不想让他们承受痛苦,所以我想帮助他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