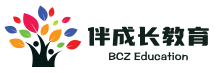今天我们采访的老家长、来自成都的余奕也是一位角色多重的妈妈。她有一个17岁的自闭症儿子玮玮,在特校的职高上高一,独生子;与此同时,余奕还是四川省残联八届主席团副主席、四川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、成都市残联执行理事、成都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、成华区政协委员。因为儿子的确诊,她十多年前就投身特教事业,开设了自己的机构。
这样一位老家长,今天分享的都是实打实的经验,以及养育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肺腑之言。这么多资源在手,余奕会怎样安排玮玮的未来也令人好奇。下面我们走进余奕的故事。
自闭症家庭的处境比想象中更难
采访余奕的时间比预想中晚一个星期,那一周,她随省残联康复处去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调研,一路所见都比预想中要更窘迫一些。
一直以来,很多家长都特别羡慕成都的自闭症孩子,几乎每个区都有特校,且特校教学水平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;小龄干预机构也很多,费用从每月3000到上万,选择余地很大;大龄上,也有“善工家园助残中心”这样的公益组织为重度孩子提供托养服务。
但同样是在四川,到了阿坝这样的地区,从家长的意识到干预资源、政策,跟省会成都一比,差距就非常大了。
大别山深处一所特校的学生,总是穿着拖鞋来上学。(一位热心的特教老师供图)
“全省3/4的机构都集中在成都了,还有1/4分散在各个市州。四川的三州指的是凉山彝族自治州、甘孜藏族自治州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,这里很多地方曾经属于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,表现在心智障碍领域,一个是康复机构数量非常少,我们调研的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县城,只有个别医院可以开展一点基础康复,且更多集中在肢体康复上,心智障碍这个板块,除了各州的州府以外,大部分县上都没有开展。”余奕介绍。
三州里,家庭条件好、年龄小的孩子有的会来成都干预;条件不好的,很多诊断就晚,有些家长直接就放弃了;个别家长被残联推荐到州府所在地干预,但时间也不会太长,可能也就半年,毕竟离家远,很多家庭还有其他孩子或老人需要照顾。
这样的现状,很多偏远地区的家长应该深有感触,这让余奕感到莫大的遗憾和痛心,17岁的玮玮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,余奕尚且没有十足的把握儿子一定能找到一份哪怕是庇护性的工作,其它孩子又将怎么办呢?
抱最好的期望,做最坏的打算
出去调研这一周,玮玮跟平时一样正常上学,由爸爸负责接送,余奕机构的老师也在帮忙,整体上玮玮还算懂事。他知道妈妈要出差,只不过这次时间有点长,玮玮看到刚回家的妈妈就把脸撇到一边去了,有点生气的意思。一直过了两三个小时,余奕主动去哄,他才缓过劲儿来。
余奕很庆幸,在成都,九年义务教育之外,还有职高可以上。以前小编就听一位大龄家长说过,如果孩子有学可上,能在融合环境里待多久就尽量待多久,因为孩子从学校出来后大把时间都会不知道怎么打发,能就业的是极少数,很多人一旦再回到家里就走不出来了,家长还要腾出一个人看护孩子,家庭负担会更重。
而且玮玮也喜欢上学,学校让他感到新鲜,学生和老师间的相处也友好而善意。特校的职高绝不是糊弄时间,玮玮学的是“家政服务”专业,但课上啥都教,生活自理、茶艺、烘焙、洗车……老师也一直在营造和灌输毕业后就要去工作的氛围和意识,告诉学生们上班要坐公交车、到了单位得打卡,各个岗位都是干什么的,还会布置家庭作业。
下午三点多,余奕把儿子从学校接到机构,上一节钢琴课或体能课再一起回家。吃完晚饭,玮玮就会进行他刻板又有趣的散步流程。
“周围有几家商场,他轮流去,今天去A商场,到电玩厅挨个投一遍篮球、买点吃的、喝的回家,明天他就会走一条纯散步路线;后天去B商场;再后天又是一条纯散步路线,穿插着来。”余奕笑着介绍。
周末,为了减肥,玮玮会跟爸爸沿着成都的环城绿道骑自行车,余奕则去机构处理工作,中午一家三口汇合吃饭,下午带去逛商场放松。
余奕对眼下的生活比较满意,作息规律,孩子每天知道干什么,情绪也比较稳定。
“这个暑假打算先找一找有没有庇护性的岗位能去实习,比如到菜鸟驿站分拣包裹,到朋友的公司看看有没有保洁的岗位,多体验一些,看看他能做什么,开学后再跟老师沟通,按照他能够做的岗位进行职业技能培训。”余奕计划。
在她看来,玮玮的一些短板(语言表达能力、理解能力)很难在一两年之内取得非常大的进步,从他未来的需求出发,这两年她会更侧重培养玮玮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,纠正他不好的习惯,比如过马路不看红绿灯(有时看有时不看);公共场合高声说话;手机公放很大声;走路不观察行人,总从别人中间穿过去等等。
另外一点是培养玮玮的主动表达意识,需要帮助时知道求助。比如感冒了要擤鼻涕,以前玮玮都是自己直接上手拿纸巾,现在妈妈就要锻炼他跟别人说:“请给我一张纸,谢谢”,先动嘴然后再动手。
“最重要的还是搭建支持环境,让周围跟他有关联的人知道他习惯的表达方式是什么,遇到问题怎样去支持他、纠正他。”余奕说。
她也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,如果玮玮连庇护性的工作都做不了,她会想方设法给玮玮创造一个岗位,比如开一家小卖部或者菜鸟驿站,请就业辅导员带着他工作。
“挣不挣钱无所谓,重点是有事情做。”余奕说。
小龄干预,先天能力占很重要的位置
跟两岁半刚确诊时相比,余奕觉得玮玮的变化非常大,现在生活上可以自己穿衣、洗碗、煮鸡蛋、削苹果,但炒菜不太行,还需要辅助。情绪在规律的生活中比较稳定,偶尔失控的时候,比如被批评和否定,会不高兴地咬袖子、原地跳、嚷嚷,但爆发频次越来越低。他机械记忆力很强,对数字敏感,记手机号、身份证号、算某年某月某日星期几特别厉害。
弱的是语言,主动表达比较差;理解能力也不好,稍微复杂的句子就听不懂了,不感兴趣的也不是很能理解。社交上,对认识的人会主动打招呼,不太关注陌生人。社会规则意识需要加强,有时会突发奇想跑到某个地方做某事(比如跑到别的楼层敲人家的门),这让余奕还不敢单独让玮玮出门太长时间,一般都需要人陪伴。
“现在已经完全接纳他了。”余奕说,刚确诊前半年是最无助的时候,因为对自闭症的认识不够,不知道这一障碍对孩子的终生有什么样的影响,她也像所有新入圈的家长一样充满希望,尽了最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康复中去,盼着玮玮恢复正常。
小时候在机构干预的玮玮
“后面学了这方面的知识,也跟更资深的家长接触之后才逐渐接受现实,自己的孩子真的跟正常孩子是有差距的,而且这个差距会终身存在,对他的规划也就变成更切实际的阶段性的小目标。”余奕说。
从玮玮确诊到上学历经4年,余奕也开了机构,在上学这件事上,她清楚地意识到,玮玮的能力达不到普校的要求,所以直接选择了特校,不像有的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读普校,不管能力是否达到,也要去试一下。“普校进去他也听不懂,特校里学的反而更有用些。”
熬成了老家长,余奕在跟新家长交流时,会建议家长根据孩子的能力做好不同阶段的规划,选对康复方向:
2.中等能力的孩子可以往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上努力,不管今后选择特校也好,普校也好,他大致能够知道每天的生活是怎样的流程,能够简单和人交流,表达自己想要什么、不要什么。成年后可以去往庇护性工厂或者日间照料中心。
3. 能力好的孩子要往独立生活和独立工作这个方向去努力。
小时候的玮玮
“在我看来,孩子今后康复得好或者不好,先天能力起决定性作用,就像不可能把一个中低智力水平的孩子提到正常水平。但不是说能力不好就不康复了,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自身能力基础上取得或大或小的进步。”余奕强调,多年从业,她发现重度的自闭症孩子越来越少,机构更多的是中轻度的孩子,大部分都可以去普小融合,但在进去之前肯定要把基础能力搭建好。
“玮玮快成年了,我们对他的培养更倾向于看他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去发掘一下,会愿意让他去报一些体育、艺术类的班,说不定今后能帮助孩子提高生活质量和就业。”余奕透露。
我现在还没想儿子今后养老的事
现在,市场上的小龄机构竞争愈发激烈,这对家长来说是好事,选择越来越多,费用却呈下降趋势。
余奕预测,今后干预的大趋势很可能是,部分康复目录进医保,医院在小龄康复市场中逐渐占据主流地位,民营康复机构要跟医院“硬碰硬”肯定碰不过,但医院也有其短板,做融合教育和社交比不过机构,而且这部分也进不了医保目录,又是很多家庭的刚需,这是民营机构自身的优势。“未来想生存下来,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”她说。
至于家长关心的康复费用能不能降,余奕认为首先要看机构目前的费用是多少,以成都的康复市场为例,每月高的有2万元的,低的也有三四千的。余奕认为,把残联补贴算进去,每月总体收费维持在3000—8000元比较合理。
“现在的家长走两个极端,一个是非常有钱的家长,不惜余力进行投入,希望孩子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;还有一部分收入中等水平的家长,会选择残联的补贴,但把干预的责任全部交给了机构,自己仍然在职场上打拼,毕竟社会压力太大了,辞职带孩子是非常困难的决定。”不管哪种心态,余奕都更加建议家长做好全生涯的规划,有的放矢。
现在她的机构已经涉足小龄和学龄业务,以后会不会做大龄,余奕的回答是:“要做,但现在还处于选方向的阶段,要跟着残联的政策走。”
她考察过很多优秀的大龄服务机构,杭州的弯湾托管中心、宁波市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以及温州的“壹星酿”面包坊,深知做大龄需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,“希望能够在政策层面上先取得一些支持,毕竟家长都知道大龄一个是不挣钱,第二可能还赔钱,所以要谨慎地选择方向。”她说,“职业培训、辅助性就业都是在考虑的,但不会去做托养服务,因为托养需要更多的资源去支持,目前条件还不太成熟。”
她觉得,大龄跟小龄市场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,都是得家长先动起来想孩子能做什么,需要政府哪些方面的支持,再找相关部门要政策,但靠政府完全兜底是兜不完的,毕竟残障群体数量太大,每个社区都建一个日间照料中心/残疾人之家,把这些孩子都收管过来不现实,况且机构也更愿意收能力好的、情绪稳定的孩子,家长想啥都不管都甩给机构,也不现实。
“还是要提前规划,现有的资源能做什么?有些家长计划着孩子以后要上大学,要结婚成家,建议不要设置过高的目标,少做太过长远的规划,目标太高会太累,容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。要多做三至五年的阶段性规划。”余奕说,她现在就不会考虑玮玮的养老问题,毕竟玮玮才17岁,未来能进步到什么程度,政策能发展到什么阶段还说不准。
这次调研,她也有一个积极的收获,在父母接纳的基础上,农村的一部分大龄心智障碍孩子过得还挺幸福。有家长带着孩子在旅游景区开民宿和农场过活,也有的自己家就有房有地,可以带着孩子边工作边生活,有事情做,反而比一些城里的家庭幸福指数更高。